 我始终记得父亲临终前的样子。
我始终记得父亲临终前的样子。
那是下午4点多的光景,放学回家,家里已经乱作一团。
父亲躺在床上,脸朝床里,好像睡得很沉,还打着呼噜。我躲在母亲身后,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懵懂无知。
屋子里还站着父亲的三个朋友,后来我才知道,他们都是西医。三个人压低声音,和母亲、祖父叮嘱些什么。我还是听见了这一句,“要是大小便失禁了,那便是情况不好了。”
父亲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。老老少少,一共有40几个人。
当晚,他就去世了,死于脑溢血,一个字都没留给我们。
第二天,上海的报纸都登出文章,报道父亲的死讯。有一家报纸做的标题是,《杭稚英身后萧条》。
杭稚英,我的父亲,解放前上海滩最著名的月份牌画家之一,那年才47岁,正是英年。
13岁考上了商务印书馆。在绘画这件事上,祖师爷赏饭吃,父亲是有灵性和天赋的。
西方人认为“13”不吉利,13却是父亲的幸运数字。
父亲生于1901年,海宁盐官人,从小聪慧过人,上海话讲起来,脑子邪气(非常)活络。
祖父很开明,没送他去读私塾,而是上了“达材学校”,不光念四书五经,也读些数理化。要赢在人生的起跑线上——祖父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。
祖父杭卓英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厂长的中文秘书,一表人才,蓄小胡子,每天出门遛马,遛着遛着,兴致一上来,居然可以站到马背上去。他的古文功底一流,书法很不错,还组建过诗社。写了很多好诗,可惜都被年幼的小弟弟折纸飞机掼光了。
商务印书馆要招练习生,相当于现在的实习生,祖父想到了儿子杭稚英。
当时父亲13岁。
商务印书馆设有裱画部——那时,祖父已经离开海宁,举家住在上海了,父亲放学回来,总是直奔裱画部,那时他已经对画画这件事入迷了。
一回家,他就把刚才看到的画面凭记忆临摹下来,临摹得像模像样。祖父颇为得意。
祖父觉得这是个机会,就推荐了这个13岁的孩子,很顺利。父亲不到弱冠之年,就成了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的实习生。
父亲进了图画部当学徒,有三个老师,一个德国老师,一个教中国画的老师,叫何逸梅,还有一个教西画的老师。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,但用来印刷的铅字,是德国人创造发明的,德文字,形状特别花哨,邪气有装饰性。德国老师主要教设计,他的课,父亲获益匪浅,父亲日后成为一个出色的月份牌画家,或者说成为中国平面、装潢设计的第一代领军人物,最初的启蒙,就来自这个德国教师。
三年学徒,父亲的表现出类拔萃,那是祖师爷赏饭给他吃。
父亲才思敏捷,服务期的第二年,就出版了单幅的月份牌广告。那年他才18岁。
按照商务印书馆的规矩,实习生三年期满,成绩优秀,就把你派到门市部去服务四年。父亲到了门市部,一下子就接触到大量的客户。
当时,商务印书馆承接的印刷量已经很大,都是类似香烟广告、电池广告的印刷业务。上海作为通商口岸,国外来的广告很多。父亲对新鲜的东西特别敏感。有一次,来了个客户,将信将疑,要这个小伙子当场画出“白象牌”电池。
表现自己的机会到了。
父亲平时就有积累,对他来说,这是小菜一碟的事。
“白象牌”电池是个很老的牌子,商标是一只胖胖的小象,像一个顽皮的婴儿。这个商标一直沿用到今天。画稿交出去的时候,客户眼睛一亮,据说父亲不但惟妙惟肖地画出了这头小象,还把象鼻子画得卷曲上翘,神态很淘气。
对父亲来说,这不仅是一张画稿,还是他做成的第一笔业务——那个客户决定把“白象牌”电池的广告印刷交给商务印书馆了。
当时,包装广告作为上海滩涌现的一个新兴的行业,客户对产品的要求并不十分明确。他们往往对产品没什么成熟的构想,全靠实习生当场绘出图样草稿。
父亲才思敏捷,出手快,又善于揣摩客户的心态,为商务印书馆争取到大量客户。
服务期的第二年,他就出版了单幅的月份牌广告。那年他才18岁。
四年后,父亲决定离开商务印书馆,自立门户。
月份牌前辈画家郑曼陀有秘不示人的技艺,父亲靠敏锐的洞察力,成功“偷艺”。
父亲很重情义,办起自己的“工作室”后,只是单纯地替人画画稿,挣稿费。遇到印刷环节,依旧把大量业务介绍到商务印书馆。
当时,大多数画家都运用中国传统工笔画的方式绘制月份牌广告,笔触细腻,但缺少活力。
而著名的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却另有一绝。他能把人的皮肤画得跟真的一样,雪白粉嫩,吹弹得破。
郑曼陀在杭州的照相馆待过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时候,有人去世了,家人就拿着死者的相片,去照相馆找画师,把死者的照片按比例放大,做成遗像。
坊间有这么种说法,说郑曼陀是“画死人”出名的,可能就是夸赞他这种出色的技法。他的上色技术是非常厉害的,自成一家。
但郑曼陀先生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,连茶房送水,他都很谨慎,会停笔不画。很多人想偷拳头,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。
父亲也曾多次登门求教,郑曼陀对父亲很客气,但每每说到要害处,郑先生就“顾左右而言他”了。
郑师母也十分配合,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,画画的工具,一样都不会落下。
但是,百密终有一疏。
终于有一次,在郑曼陀家的茶几上,放着一只小小的玻璃瓶,里面装着细密的粉末,发出幽暗的紫光。父亲眼尖,偷偷留意了一下,发现是炭精粉。
炭精粉那时候是照相馆用来修版用的,上海话叫“擦铅照”。父亲不动声色,回家后,拿炭精粉试验了好几次,终于,那种逼真的效果出现了。
原来,郑先生的“秘密武器”就是它。
父亲把自己的新作品拿给郑曼陀过目,郑曼陀脸色微微一变,但依旧很沉得住气。他拿着父亲的画,和夫人一起走进里面的房间,半天才出来,用苏州话淡淡地对父亲说,“倷(你)画得不错,蛮好,蛮好。”再没多说什么。
炭精粉究竟起到了什么有如神助的作用?这神秘的紫光,保证了擦笔画打好的画稿色调偏冷,再罩上水彩画颜色,冷暖相宜,画面不脏、不暗,效果奇好。
月份牌上的美女服饰,几乎成了当时上海名媛佳丽的流行风向标。外乡女人也效仿。
艺术家都期望自己的作品,在问世的那一瞬间,能吸引住人们的眼睛。用上海话说,叫做“弹眼落睛”。
父亲时刻在动脑筋,让中国的月份牌画看上去有更出色的视觉效果。
他去看电影,当时全部是无声电影,就是默片,只有“华纳迪斯尼”公司的动画电影是彩色的,非常生动,在父亲看来,就有一种“弹眼落睛”的冲击力。
他就天天往电影院跑,看美国动画电影的色彩运用。
他还从天津的杨柳青年画、四川绵竹的灶王爷画中学习用色的方法,敢于用那种很鲜艳的染料。
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,那种桃红柳绿的染料,显然是绵薄的中国宣纸所承载不动的,父亲又折腾开了,开始托人去国外买进口的印刷纸。
画室的运作越来越完善,杭稚英的名声愈发响亮了。
画室的房子是租来的,在山西路海宁路口,一套三进的天井房子,原来据说是前清一个官员的大宅,后来由几个资本家联合买下来,变成江浙皖丝茧公会。三进中国式院落,门口有两个石狮子,很气派。
房子的结构很奇特,一半西式,一半中式。父亲租了那里四分之三的房子,一共有40个房间,家里有七八个佣人,还有专门的“梳头姨娘”,用刨花水刷头发,用棉纱线刮脸。一起开饭,要坐满5桌人。
家里有地毯、摇椅、沙发,装了4门电话,十分洋派。
对那幢大房子,我最深的印象是,各种各样进口的期刊,从《life》、《Esquires》到数不清的服装设计杂志,全是父亲从国外订购的,家里看上去简直就像个外国图书馆!
父亲不懂外语,但那些原版的期刊,让他始终走在时尚前沿。
父亲有一部很潮的脚踏车,那时候,脚踏车是非常稀奇的舶来品。他会打高尔夫,有一张作品,是两个卷发旗袍女子在打高尔夫,到今天看来,也觉得时髦、新鲜。
他还有一台照相机,是德国的“劳斯莱斯”,方形,双镜头反光,他曾经用这个相机,以孤山边上的西泠印社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。
这么时尚,他的创作当然就与众不同。父亲笔下的月份牌美女十分新潮,旗袍开衩的高低,旗袍领口的宽窄,露多少面积的胳膊,露多少脖子,旗袍上的图案是方格子还是碎花,是藤蔓还是团锦,几乎成了当时上海滩名媛佳丽们的流行风向标。外乡的女人们也在偷偷效仿。
原先免费派送的月份牌,一下子变了发布时尚信息的媒体,商家们越发来劲了,父亲的订单越来越多。
父亲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可观,有800银元的收入,远远高于洋行买办、高级白领。
父亲十分讲究仪表,他的衣服,布料都从“信大祥”买,他做西装,都是裁缝来家里量尺寸的。记得父亲有件衬衫,袖口做得十分考究,袖扣是金子和翡翠搭配起来做的。每一条西裤的裤线都烫得笔直,这种细节,父亲从来不肯马虎。
因为那是个只认衣衫不认人的社会,父亲的很多开销都花在这些地方。
据我的姨夫李慕白回忆,那几年,父亲进入事业顶峰期,人手根本忙不过来,李慕白和父亲的同学金雪尘,就在那个时候加盟画室了。
李慕白和金雪尘,也是中国月份牌画坛上的两员大将。李慕白擅长油画,对印象派很有研究,金雪尘的风格是中西皆备,尤其擅长画景。
父亲和他们两位的合作方式十分奇特,常常是一张白纸上,李慕白先画人物,画到八成,金雪尘就能在人物之后配上景物,同人物先后呼应,最后由父亲作整体调整、润色,配合得天衣无缝,像是一个人画出来的。
今天看,就带点儿“工作室”的雏形了。
在这样一个合作紧密的团队里,出品就比较快了,一年能画80多张。
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结棍(厉害),有800银元的收入。当时上海的洋行买办,高级白领,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300银元。
依父亲的收入,买辆汽车已经绰绰有余。当时,上海滩很多人还买不起汽车,黄金荣、杜月笙也只有一辆四匹马的马车,已经算是阔佬级别。但父亲没有买汽车,他买了一辆私人黄包车,用来出行,他其实相当节俭。
父亲要养活一大家子,40几号人,每天要开伙,有点“孟尝君,食客三千”的味道。画室成员和他招收的学徒,都住在我家里,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。
画室实行按劳分配,很公平。
学徒们总受父亲的鼓动,经常在一起踢足球,办家庭舞会,父亲觉得,要是学徒们的业余时间没有娱乐活动,他就非常不安心。
李慕白画艺日渐长进,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,就送他到有名的西洋画社团去深造。
父亲善于接受新技巧,现在叫“与时俱进”。
照相馆修底版用的喷枪,人工打气的,父亲会想到拿来用在绘画稿中,用来调匀色调。佣人给他打气,扑哧扑哧打足了,父亲喷上一阵子,气没了,佣人再打。
他用的也是最好的进口喷枪,所以,画的色调特别柔和。
他发现挪威产的卡纸,又叫“马头纸”,肌理细腻,纸基坚实,又发现美国出品的16盒装水彩色相很鲜亮透明,就直接从挪威和美国订购。
父亲也不保密,掌握了什么新鲜技术,都会告诉别人。
他与同道之间的关系相当随和、有亲和力,对师徒关系也看得很超脱。
那年头,从师就必须从一而终,像婚姻,这是铁定的规矩。有个国画家,他一个学生改拜别的画家为师,国画家大怒,一气之下,登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,两人彻底闹僵。
父亲不是这样的。后来李慕白的画艺日渐长进,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,就出钱把他送到当时很有名的西洋画社团“白鹅画室”去深造。
李慕白学成后,依旧回到父亲的画室工作,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了。
李慕白16岁就来我家学画了,他说,我生是杭家的人,死是杭家的鬼。
父亲最早在商务印书馆的国画老师何逸梅,后来也成了画室中的一名成员,抗战爆发后,他跑到香港去了,在那里模仿父亲的月份牌画,一时有“香港杭稚英”之称。父亲知道后,也并不介意。
后来香港也被日军占领,“港漂”何逸梅又回到上海,父亲照样接纳他,专门在家里为他搭了一个阁楼,老婆孩子一家都接来住了。
拒绝给日本人画东亚共荣圈的画,画室的运作突然停滞,一大家子只能靠借钱度日。
黄金荣60大寿那年,要父亲给他画像。
上海滩上,但凡有人要开店,店堂里就要挂一张黄金荣的画像,这样,地痞流氓就不敢上门欺负了。
但是黄金荣很不好画,因为他一脸麻子,画出来也不美。要是美化他了,把他的脸画光卷漂亮了,又像拍他马屁一样。父亲不愿意给人这样的感觉。
父亲对来人说,我不会画男人,只会画女人。然后就逃到苏州避难去了。
抗战爆发,日本人占领上海,他们知道父亲是画界的名人,想让他画大东亚共荣圈的年画,画日本和服美女。
家里来了个矮矮的日本军官,带来了20根金条,一根10两重,等于是二百两黄金。
父亲有自己的节气,也不想和日本人起正面冲突,那个军官带兵来的,都是关东军。
他有气管炎的毛病,平常咳得重一点,痰里会有鲜血。那天,父亲拼命咳拼命咳,咳得手发颤,手帕里都是血,一副病态。他和日本军官说,我这样的身体是没办法画画的。
日本人也没办法,他们也不硬来,就扬长而去了。
父亲工作室的收入完全是是靠画画稿的,这样一来,他也不敢再接别的画,一大家子从此断了收入来源,只能借钱度日。
母亲去买“户口米”,是要编号和排队的,那点米,40几口人怎么够吃。母亲就和佣人去北火车站那里,那里每天有从无锡农村来的小贩,他们卖米,还卖点番薯杂粮。
这么时尚,他的创作当然就与众不同。父亲笔下的月份牌美女十分新潮,旗袍开衩的高低,旗袍领口的宽窄,露多少面积的胳膊,露多少脖子,旗袍上的图案是方格子还是碎花,是藤蔓还是团锦,几乎成了当时上海滩名媛佳丽们的流行风向标。外乡的女人们也在偷偷效仿。
原先免费派送的月份牌,一下子变了发布时尚信息的媒体,商家们越发来劲了,父亲的订单越来越多。
父亲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可观,有800银元的收入,远远高于洋行买办、高级白领。
父亲十分讲究仪表,他的衣服,布料都从“信大祥”买,他做西装,都是裁缝来家里量尺寸的。记得父亲有件衬衫,袖口做得十分考究,袖扣是金子和翡翠搭配起来做的。每一条西裤的裤线都烫得笔直,这种细节,父亲从来不肯马虎。
因为那是个只认衣衫不认人的社会,父亲的很多开销都花在这些地方。
据我的姨夫李慕白回忆,那几年,父亲进入事业顶峰期,人手根本忙不过来,李慕白和父亲的同学金雪尘,就在那个时候加盟画室了。
李慕白和金雪尘,也是中国月份牌画坛上的两员大将。李慕白擅长油画,对印象派很有研究,金雪尘的风格是中西皆备,尤其擅长画景。
父亲和他们两位的合作方式十分奇特,常常是一张白纸上,李慕白先画人物,画到八成,金雪尘就能在人物之后配上景物,同人物先后呼应,最后由父亲作整体调整、润色,配合得天衣无缝,像是一个人画出来的。
今天看,就带点儿“工作室”的雏形了。
在这样一个合作紧密的团队里,出品就比较快了,一年能画80多张。
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结棍(厉害),有800银元的收入。当时上海的洋行买办,高级白领,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300银元。
依父亲的收入,买辆汽车已经绰绰有余。当时,上海滩很多人还买不起汽车,黄金荣、杜月笙也只有一辆四匹马的马车,已经算是阔佬级别。但父亲没有买汽车,他买了一辆私人黄包车,用来出行,他其实相当节俭。
父亲要养活一大家子,40几号人,每天要开伙,有点“孟尝君,食客三千”的味道。画室成员和他招收的学徒,都住在我家里,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。
画室实行按劳分配,很公平。
学徒们总受父亲的鼓动,经常在一起踢足球,办家庭舞会,父亲觉得,要是学徒们的业余时间没有娱乐活动,他就非常不安心。
李慕白画艺日渐长进,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,就送他到有名的西洋画社团去深造。
父亲善于接受新技巧,现在叫“与时俱进”。
照相馆修底版用的喷枪,人工打气的,父亲会想到拿来用在绘画稿中,用来调匀色调。佣人给他打气,扑哧扑哧打足了,父亲喷上一阵子,气没了,佣人再打。
他用的也是最好的进口喷枪,所以,画的色调特别柔和。
他发现挪威产的卡纸,又叫“马头纸”,肌理细腻,纸基坚实,又发现美国出品的16盒装水彩色相很鲜亮透明,就直接从挪威和美国订购。
父亲也不保密,掌握了什么新鲜技术,都会告诉别人。
他与同道之间的关系相当随和、有亲和力,对师徒关系也看得很超脱。
那年头,从师就必须从一而终,像婚姻,这是铁定的规矩。有个国画家,他一个学生改拜别的画家为师,国画家大怒,一气之下,登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,两人彻底闹僵。
父亲不是这样的。后来李慕白的画艺日渐长进,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,就出钱把他送到当时很有名的西洋画社团“白鹅画室”去深造。
李慕白学成后,依旧回到父亲的画室工作,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了。
李慕白16岁就来我家学画了,他说,我生是杭家的人,死是杭家的鬼。
父亲最早在商务印书馆的国画老师何逸梅,后来也成了画室中的一名成员,抗战爆发后,他跑到香港去了,在那里模仿父亲的月份牌画,一时有“香港杭稚英”之称。父亲知道后,也并不介意。
后来香港也被日军占领,“港漂”何逸梅又回到上海,父亲照样接纳他,专门在家里为他搭了一个阁楼,老婆孩子一家都接来住了。
拒绝给日本人画东亚共荣圈的画,画室的运作突然停滞,一大家子只能靠借钱度日。
黄金荣60大寿那年,要父亲给他画像。
上海滩上,但凡有人要开店,店堂里就要挂一张黄金荣的画像,这样,地痞流氓就不敢上门欺负了。
但是黄金荣很不好画,因为他一脸麻子,画出来也不美。要是美化他了,把他的脸画光卷漂亮了,又像拍他马屁一样。父亲不愿意给人这样的感觉。
父亲对来人说,我不会画男人,只会画女人。然后就逃到苏州避难去了。
抗战爆发,日本人占领上海,他们知道父亲是画界的名人,想让他画大东亚共荣圈的年画,画日本和服美女。
家里来了个矮矮的日本军官,带来了20根金条,一根10两重,等于是二百两黄金。
父亲有自己的节气,也不想和日本人起正面冲突,那个军官带兵来的,都是关东军。
他有气管炎的毛病,平常咳得重一点,痰里会有鲜血。那天,父亲拼命咳拼命咳,咳得手发颤,手帕里都是血,一副病态。他和日本军官说,我这样的身体是没办法画画的。
日本人也没办法,他们也不硬来,就扬长而去了。
父亲工作室的收入完全是是靠画画稿的,这样一来,他也不敢再接别的画,一大家子从此断了收入来源,只能借钱度日。
母亲去买“户口米”,是要编号和排队的,那点米,40几口人怎么够吃。母亲就和佣人去北火车站那里,那里每天有从无锡农村来的小贩,他们卖米,还卖点番薯杂粮。

杭鸣时介绍父亲创作“美女月份牌画”背后的故事
(来源:中国炭精画世界/作者:杭鸣时)
责任编辑:文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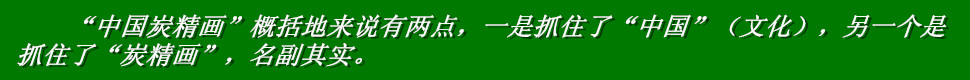

评论列表: